约拿单·爱德华兹对自然世界着迷。他从小就经常分析他周围的世界,认为 “自然与普遍性护理之书”显明了他所敬拜这位造物主的诸多属性(《约拿单·爱德华兹作品集》,第11卷,50页)。爱德华兹对圣经中的预表和“神圣事物的影子”的关注是这位北安普顿牧师的持久遗产的一部分(51页)。因此,在70多年前,学者们就开始对其作品进行注释和编辑。设在耶鲁大学的约拿单·爱德华兹中心最终出版了26册纸质书,然后将注意力转向电子版本的制作。
除了这些学术上的努力,诸如“真理旌旗”(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和“渴慕神”(Desiring God)这些跨教会机构也致力于在教会中推动阅读爱德华兹的著作。他们共同为仰慕这位可以说是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的新一代铺路。这些“年轻、躁动的改革宗”福音派基督徒发现,爱德华兹绝不仅仅是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他是一个英雄。
英雄的问题是,他们的斗篷会起皱。简而言之,他们会让我们失望。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不足并决定如何应对。
爱德华兹也不例外。事实上,他的某些失败会变得格外显著,这在人们试图使用带着注释和批判性文字的版本以更清楚地了解他的生活和思想时尤为凸显。也许爱德华兹所犯的错误中最有问题的是他对基于种族的奴隶制有着全面性的参与。不管如何为他辩护,爱德华兹这个奴隶主离我们希望的英雄颇有距离。然而,历史上的爱德华兹不仅促使我们拒绝把他仅仅当作精神遗产和心目中的英雄,而且让其他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思想家,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和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帮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力量,以促进有意义的反思和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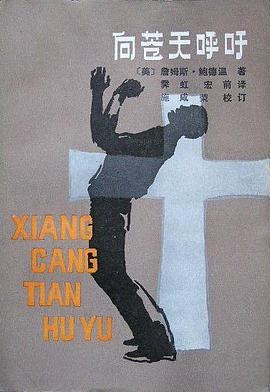 詹姆斯·鲍德温以半自传体著作《向苍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台译《山巅宏音》)登上文坛,该书聚焦于哈莱姆居民约翰·格莱姆斯的生活以及他与家庭、教会和信仰的脆弱关系。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继续在《乌木》特刊中处理历史研究的问题。在《白人的罪疚》(“The White Man’s Guilt”)一文中,鲍德温谈到了历史研究的实践,不仅对这一学科的前景作出意义深远的解释和反思,而且说明了将其简化为重述遗产和简化版英雄故事的危险性。作为一名美国的种族史学家,我发现鲍德温对历史学科的危险和作用的论述极具指导性和挑战性。
詹姆斯·鲍德温以半自传体著作《向苍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台译《山巅宏音》)登上文坛,该书聚焦于哈莱姆居民约翰·格莱姆斯的生活以及他与家庭、教会和信仰的脆弱关系。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继续在《乌木》特刊中处理历史研究的问题。在《白人的罪疚》(“The White Man’s Guilt”)一文中,鲍德温谈到了历史研究的实践,不仅对这一学科的前景作出意义深远的解释和反思,而且说明了将其简化为重述遗产和简化版英雄故事的危险性。作为一名美国的种族史学家,我发现鲍德温对历史学科的危险和作用的论述极具指导性和挑战性。
鲍德温没有说一些历史总是在重复之类的废话,他敏锐的分析令人信服:
几乎没有人知道,历史不仅仅是用来读的。而且,它不仅仅指向过去,甚至也不是在原则上指向过去。相反,历史的巨大力量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带着它,在许多方面无意识地受它控制,而历史也确实存在于我们所做的一切之中。(《乌木》特刊,47页)
如此看来,历史对所有人为自由和公义所做的挣扎都大有裨益。历史帮助我们确定自由和公义是什么、不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鲍德温断言,“正是由于历史,我们才有了我们的参考框架、我们的身份和愿望”。(47页)历史不仅仅被当作“过去”对待,它也在不断塑造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生活,需要将其与遗产分开。
虽然并不总那么明确,但与“历史遗产”相关的呼声在最近几个月和几年中重新响起。当美国白人抗议真正的历史遭到抹杀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时候并没有真正指向历史。相反,他们是在用“历史遗产”的概念来代替,而这种“遗产”只不过是一种扭曲的历史感而已。如果你愿意,这就是一个被替换的现实。与鲍德温谈论的历史不同,遗产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存在。遗产可以在方便的时候与我们的行动分开。有意将遗产误标为历史近来似乎很常见。这种混淆使我感到忧愁。
我的悲伤源于我们愿意在这种虚假之上发展,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就能从中获利,即或不然我们就躲起来。然后,即使我们“朦胧地或生动地意识到(我们)喂给自己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谎言”,正如鲍德温所感叹的那样,但我们不仅坚持,而且还致力于为其开脱,因为我们在整个社会共同认知的故事中出局了。鲍德温预言道(47-48页):
这种“出局”的性质可以简化为一种恳求:不要怪我,我不在那里。我没有做过。我的历史与欧洲或奴隶贸易毫无关系。无论如何,是你的酋长把你卖给了我。我没有经手,我不对曼彻斯特的纺织厂或者密西西比的棉田负责。此外,想想英国人在那些纺织厂和那些可怕的城市里是如何受苦的!我也鄙视那些总督。我也鄙视南方各州的州长和南方各县的警长,我也希望你的孩子能受到体面的教育,并在他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升到最高。我没有针对你,没有!我没有针对你。为什么你还要对我不满呢?你想要什么?
有了这种维护遗产——而不是历史——的糟糕努力,我们很容易发出信号,为自己、我们的遗产和英雄辩护。
了解了鲍德温对历史和遗产之间区别的解读,我们可以回到爱德华兹。我们常常倾向于捍卫我们的遗产和英雄,甚至超过捍卫我们自己。这几乎就像在相信除非我们奉承他们,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相反,我们这样做最终会摧毁这些英雄和我们自称热爱的过去。
一种比较大众化的扁平化某些历史人物的方式就是把他们抽象化。我们何时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当我们被迫去面对他们生活中那些不那么令人满意的部分时,常常会把英雄们抽象化。正如温德尔·贝瑞提醒我们的那样,“无论在哪里,抽象都是敌人。”当我们把一个英雄描述为“他时代的人(注意,几乎总是一个人)”时,贝瑞的说法再真实不过了。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就像一个敌人,使人和历史都被扁平化。
我们把英雄扁平化的另一种方式是有意识地忽视或有时忽略他们的失败,因为我们所谓的未知拒绝处理我们已知的东西。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分析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宗教信仰和种族构建的交集。我试图把重点放在我们可以知晓的那段时间和那个地方的一些主要人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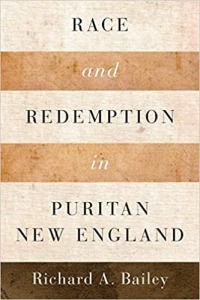 从一开始,没有人比爱德华兹更吸引我的注意力。他出现在我的《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种族与救赎》(Race and Redemption in Puritan New England)的每一章中。由于我无法在这里充分探讨所有这些内容,我将利用这个机会鼓励你更全面地探讨我的书。不过,我确实想指出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爱德华兹的几个事实,以及他在北安普顿国王大道的房子里参与奴役其他人类的做法和以种族主义的姿态对待他的黑人和原住民邻居这一过程。
从一开始,没有人比爱德华兹更吸引我的注意力。他出现在我的《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种族与救赎》(Race and Redemption in Puritan New England)的每一章中。由于我无法在这里充分探讨所有这些内容,我将利用这个机会鼓励你更全面地探讨我的书。不过,我确实想指出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爱德华兹的几个事实,以及他在北安普顿国王大道的房子里参与奴役其他人类的做法和以种族主义的姿态对待他的黑人和原住民邻居这一过程。
首先,约拿单·爱德华兹一直把非洲男人、妇女和儿童视为个人“财产”。这种想法可以从他为自己和他人购买人口和租借奴隶中看出。例如,在1731年订立的一份卖身契中,这位年轻的牧师买下了一个名叫维纳斯的年轻女孩——他认为是属于个人财产的至少七个人中的第一个。在这一常规法律交易之后,他又采用了另一种奴隶主惯常的做法,就是将维纳斯改名为利亚。这样一来,这个14岁的女孩立马就从希腊的爱神变成了圣经中不被爱的妻子——再次将她的身份定为低人一等。
关于奴隶主爱德华兹的另一个事实是,他(和他的父亲提摩太·爱德华兹一样)参与了租借奴隶的贸易。将人租借给社区里的其他人可确保奴隶主的投资得到回报。正如爱德华兹的妻子撒拉写给镇上警察的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爱德华兹确实把利亚租了出去,可能是为了补贴他经常被拖欠的工资。利亚被租借出去也表明,爱德华兹与大多数新英格兰人一样,将受奴役的妇女视为家庭的一部分。在她给警官的信中,撒拉请他转达她和她的孩子们"对利亚的爱"。这样的感情表达说明了有关爱德华兹参与奴隶贸易的另一个事实。他和他的家人与奴隶建立了情感上的纽带,即便与此同时他以一种种族主义的姿态对待他们。
尽管为利亚创造了这样一个身份,这个以前被称为维纳斯的年轻女孩还是在1736年加入了北安普顿教会。因此,我们得知有关爱德华兹种族思想的另一方面是:他欢迎新英格兰的有色人种进入当地的属灵共同体。他接纳黑人归信者成为正式的教会成员。在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大觉醒”的复兴时期,这种身份对有色人种来说更加普遍,其中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可以参与当地教会的生活。例如,爱德华兹在给人施洗前的教导记录包括他对黑人初信徒提出的具体问题。
黑人教会成员也可以在对白人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出面指证那位白人成员。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提到于1744年发生在年轻人中间的圣经争论中出现了这样的证词。在发现一些年轻的白人男子利用助产手册骚扰社区妇女后,塞斯·波默罗伊少校的非洲奴隶巴斯希巴作证,指控提摩太·罗特和他的同谋者(马斯登,292页)。因此,一个黑人的声音帮助了会众对犯罪者悔改的呼吁。
我们还知道,爱德华兹为其他奴隶主辩护,并含蓄地为自己辩护。在1740年代初,他替一位陷入争议的“旧光派”牧师本杰明·杜利特尔(Benjamin Doolittle)起草了一封信。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的会众试图(第三次)罢免杜利特尔,他们声称,他不适合做他们的道德和属灵领袖。指控是什么?杜利特尔是个奴隶主。爱德华兹应要求为杜利特尔和奴隶制辩护。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明确表示,虽然他支持奴隶制,并从奴隶制中受益(就像大多数新英格兰白人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一样),但他认为海外奴隶贸易及其绑架人的做法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在为这一自己不喜欢的神学立场辩护的时候(他最终给被奴役的阿比雅·普林斯发了工资),他也说明了对基于种族的奴隶制中某些因素感到不快。
在他买下维纳斯后不久写的一篇私人文章中,爱德华兹明确表示,他对奴隶主经常虐待被他们视为私有财产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感到不安。他的“空白圣经”中一个条目暗示了他在如何对待这些人方面的挣扎。最初,爱德华兹写道,约伯记31:13-14“清楚地说明了我不应该轻视和虐待他人的原因”。爱德华兹也许是对他的解经过于个人化而感到不舒服,就再编辑了他的注释,解释“为什么约伯不应该轻视和虐待他的仆人”。这位永远谨慎细致的遣词造句者的修改表明他有时会对作为奴隶主所带来的问题感到挣扎。
爱德华兹在这方面并不是特例。例如,他的表弟(有时也是巡回布道的伙伴)司提反·威廉姆斯也记录了他自己在对待奴隶方面的挣扎。威廉斯在担任马萨诸塞州朗米多的牧师时,写了60多年的日记。在日记中,他经常记下自己身为奴隶主的做法,包括几个具体的地方提到他在精神和身体上虐待非洲男性奴隶,至少有两个人被逼自杀。
约拿单·爱德华兹也有类似的行为吗?有可能。不过,我们从他的“空白圣经”手稿中得知他可能与奴隶发生过肢体冲突,这些互动可能使爱德华兹本人也受了伤,温德尔·贝瑞将其描述为隐藏的伤口。
我们不必把爱德华兹抽象地看为“他那个时代的人”,或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辩护。相反,我们应该在他明显犯错的时候对他进行批评。他一生参与基于种族的奴隶制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即使是无意的,爱德华兹也促成了我们国家和教会中的一些种族主义的基础:一个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经济稳定的国家,以及由虽然共同敬拜但彼此根本不平等的成员组成的教会。当他所说的神学和教义是正确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保持向他学习的意愿。
这样的坚持希望能说明,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停止阅读爱德华兹或研究他的生平和作品。话虽如此,但经过二十年来了解爱德华兹的一些想法和行动如何导致灾难、种族主义、虐待和奴隶的死亡,我理解并尊重选择不同方法的人。尽管如此,我不认为这样的路线对约拿单·爱德华兹(和许多其他历史人物)是最好的。相反,我认为我们可以、也应该向他学习。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愿意承认他做错的地方,并明确地予以谴责。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爱德华兹的榜样。当他认为他的英雄们犯错时,他就会说出来。即使这个英雄是他通常被称为“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教皇”的外祖父和导师所罗门·斯托达德。即使这种立场最终以他在1750年被北安普顿的教会开除而告终。在这样的时刻,爱德华兹预见到了詹姆斯·鲍德温的想法,并建议如何对待历史及其不完美的演员。但是,即使他在与教会有关的重要问题上与斯托达德意见相左,爱德华兹也没有试图推翻他导师一切的教导,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工作比斯托达德更重要。他在1739年透露了这样的想法,当时他讲了一系列以历史为主题的30次布道,一再指出他所敬拜的上帝是如何利用不完美的男女信徒来完成超越自己的工作。在他看来,这些人并不是故事中的英雄。相反,爱德华兹认为,唯一的英雄是救赎人们的上帝。
约拿单·爱德华兹过着一种信心的生活。虽是不完美的生活,但还是一种信心的生活。而且,正如斯科特·哈夫曼所言,信心的生活教导人们很多有关赐下应许的神的功课。或者,引用1739年在爱德华兹死后出版的《救赎大工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系列中的概念,对历史的研究中揭示了许多关于救赎的内容。爱德华兹在分析过去,向他们指出改变未来的可能性时,并不关心如何奉承在北安普顿的会众或他的前辈。他很可能赞同鲍德温的说法,即“那些想象着被历史恭维的人(确实如此,因为他们写了历史),就像针上的蝴蝶一样被钉在历史上,无法看清或改变自己和世界”(《乌木》特刊,47页)。因着对圣经中的预表感兴趣,爱德华兹可能会把被刺穿的蝴蝶解释为他所敬拜的上帝通过十字架的工作救赎选民的影子,他认为通过拔掉针,历史的上帝在世界中实现了真正有意义的改变。
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仅要把约拿单·爱德华兹看作是一个英雄。他生活在历史中。有时他成功地做到了马太福音22:34-40中上帝的律法。在其他时候,他却失败了。他在种族和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无疑没有践行爱上帝和爱邻舍的诫命。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失败中学习。
认识到正面且具体的历史力量,并拒绝接受令人愉悦的遗产替代现实和抽象的英雄,这不仅使我们做好准备处理过去和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而且做好准备面对现在和未来。面对种族偏见和白人至上主义,这种研究种族具体历史问题的方法不仅使我们能够处理种族主义对个人和系统造成的真正创伤,而且还能够促进实际的变革和种族正义。
译:SJH;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Should I Still Read Jonathan Edw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