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系“美国文化战争”系列文章的第四篇。
我们的社会在对待基督信仰上真的已经做出了决定性的转变吗?我们是否已经抛弃了一个对基督信仰基本持正面态度的文化世界,进入了一个对基督信仰持消极负面态度的文化世界?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应该让承认这种文化转变成为我们看待自己——作为坚定的基督徒——与周围文化之间关系的正确视角?
亚伦·雷恩(Aaron Renn)在他为《要事第一》(First Things)网站撰写又广为流传的文章中探讨了这种从积极到消极的转变,我在前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到了这一点,那是我关于新宗教右派崛起和美国文化战争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三篇。该系列的前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美国文化战争的历史和脉络,以及将信念与文明礼貌切割的趋势。
让我复习一下。雷恩的分类法是这样的:美国文化在1994年之前对基督教基本持积极正面态度,94年之后的20年里对基督教基本持中立态度,但自2014年以来,美国文化对基督教转为消极否定的态度。我注意到,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和澳大利亚牧师斯蒂芬·麦卡尔平(Stephen McAlpine)都指出,文化转变也是在那个时期发生的。
雷恩的分类法为开启这个话题做了很好的努力,因为(1)很难否认过去10年的快速文化转变,(2)雷恩的框架暗示了一种结论,即以前参与文化的方式现在已经过时了,也许适合以前的时代,但不再有意义了。
但雷恩的文章并没有提供一个处方,如新的战略或新的战术;相反,它提供了对这一文化时刻的描述,从而促使福音派人士开辟一条新的路线。事实上,雷恩认为有太多人仍然生活在过去,假设世界对他们来说仍然是积极的或中立的。他写道:
福音派人士不应该将已有的战略延伸到未来,而是可以而且应该认真地探讨他们生活在一个对基督信仰消极负面的世界中意味着什么。这个时代应该采用什么策略?与以前的时代不同,我们需要各种方法来回应美国基督徒所处的各种情况。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可能需要试错,以及一组具有不同技能和感觉的新领袖。
今天,我想指出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些局限性,因为我相信我们所处的时刻比雷恩的构思和可能的建议更加复杂。在本系列下一篇文章中,我将谈谈我认为这种方式最明显的弱点是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问,2014年是否是一个好的里程碑。生活在一个敌视基督教的世界中这种“感觉”是最近才有的吗?
作为一个在致力于宗教右派宗旨和目标的家庭中长大的人,我认为我们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处于一个对基督信仰有敌意的世界了,这甚至是在雷恩声称我们从正面转向中立之前。我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卡曼(Carman)的歌创作于1992年——它记录了美国滑向无神论的过程,并声称这个国家要度过这十年,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复兴中回到神身边。
如果我能回到过去,告诉青春期的自己,其实你仍然处在一个对你的信仰持积极态度的世界,但文化即将转变为对基督教持中立态度,我相信我会被以前的自己嘲笑,也会被我的家人嘲笑。像当时大多数福音派教徒一样,我们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对基督持负面态度的世界里。而我又是在圣经地带长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雷恩提出的分类法保持怀疑——不是因为它们没有价值(它们几乎总是有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几乎总是太整齐,而且它们通常与某种旨在动员选民集团的提案有关。政治参与成为实现社会变革的最重要杠杆。(明确地说,雷恩的文章并没有这样做,但许多以他的工作为依据的回应者却这样做了。)
也许逼迫的空气是想象出来的,也许我们在90年代初担心的那些可怕的情况被夸大了,雷恩是对的——我们当时是被愚弄了,以为世界对我们是负面的,而实际上,我们只是对从积极到中立的变化做出反应。但是,在这样一个可能是想象出来的文化中长大,这一氛围对我们的文化参与方式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教会履行其使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我13到14岁的时候,我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讲述2050年的基督徒因为受逼迫而被赶出美国。)
更重要的是,后来我去世界其他地方旅行,与那些经历过政治压迫和真正信仰逼迫的人交流,才让我看到了更广泛的基督徒关注的问题,当我把注意力放在选举获胜上时,很多问题都被我出于方便忽略了或忽视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仍然同意青少年时期的自己所持有的原则和应对,但我对基督徒的关注范围已经扩大,我对通过政治进行文化变革的期望也得到了修正。
因此,即便我认识到雷恩、凯勒和麦卡尔平指出的过去10年中文化情绪的转变,我还是对采用“消极负面态度的世界”这一框架犹豫不决,因为不管它有什么优点,我已经很容易看到它如何缩小我们的关注范围,扭曲我们对圣经的解读。
“但是,”你可能会说,“那些试图在政治上保持‘超越’的文化参与派也对圣经有扭曲的解读,对吗?”没错,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点:我们都倾向于从我们试图接触的人那里获取线索。
雷恩的文章批评了与文化互动的那一派采取的策略,即从世俗精英的共识中“取材”。为了吸引世俗精英或名人来到他们的教会,许多抵制老牌宗教右派的文化参与型牧师以“向右出拳,向左拥抱 ”而闻名。换句话说,你想接触世俗和精英,而你这样做的方式是分享一种对其他阶级或阶层的蔑视感,他们不值得或不接受主流文化的青睐。
因为感受到左派精英们的压力,文化参与型领袖们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找“同步”他们观点的方法,而种族和移民成为两个最明显的接触点。“他们在这些领域的言论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与世俗的政治立场相一致,”雷恩写道:
同时,他们在热点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和言辞进一步软化。他们经常谈论全面支持生命,而较少谈论子宫里的孩子。在坚持关于性的传统教义的同时,他们倾向于少谈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多谈教会应该如何成为一个欢迎“性少数”的地方,强调教会过去在这方面的失败。
我并不怀疑这种压力的存在,而且一些文化参与型基督徒可能,甚至是无意地,在他们可以的时候与世界“同步”这些立场。年轻的文化战士们在攻击这一类的试探上是正确的。
话虽如此,好斗的文化战争拥护者最终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但方向是相反的:向左打压,向右拥抱。如果你试图接触到经常感到被遗忘的那部分人——他们联合起来蔑视“左派”或“精英”——你会感到另一种压力,要把你的关切与右翼播客和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同步。你关注的优先次序将首先转向离你近的人群。在这种情况下,打击种族不公正或回应《圣经》中关于关心客旅和寄居者的命令,很可能在你的道德责任列表上没有那么高的分数。文化斗士们也不能避免在某些领域弱化圣经命令的诱惑,以避免触犯社区内人们的敏感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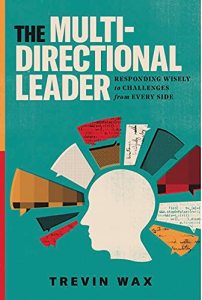 我在《多个面向的领袖》(The Multi-Directional Leader)一书中列举了这种倾向的例子。西岸的一位牧师计划在公开祷告的时候提到堕胎的罪恶,结果遭到了他手下的反对——他们担心一些来访者会受到冒犯。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没有人质疑他在以前的牧祷中所传递的基督徒对移民的关怀或我们国家的种族不公正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南方圣经地带的一位牧师却经历了相反的情况,教会成员期望牧师为结束堕胎祷告,但当祈祷集中在枪击受害者、移民或种族歧视受害者身上时,他们就会变得紧张。(“我们牧师是不是左派?”)
我在《多个面向的领袖》(The Multi-Directional Leader)一书中列举了这种倾向的例子。西岸的一位牧师计划在公开祷告的时候提到堕胎的罪恶,结果遭到了他手下的反对——他们担心一些来访者会受到冒犯。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没有人质疑他在以前的牧祷中所传递的基督徒对移民的关怀或我们国家的种族不公正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南方圣经地带的一位牧师却经历了相反的情况,教会成员期望牧师为结束堕胎祷告,但当祈祷集中在枪击受害者、移民或种族歧视受害者身上时,他们就会变得紧张。(“我们牧师是不是左派?”)
想象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世界对我们的姿态会影响我们的见证。不加批判地采用我们处于一个“对我们持有敌意的”世界这一观点,会导致我们回避不稳定的问题,通过缩小圣经的范围来损害福音对文化所发出挑战的广度。如果认为教会的使命只集中在“寻求巴比伦的平安”上,可能会导致我们对文化的塑造程度感到天真。但是,如果把教会的使命主要集中在反抗或重新获得统治地位上,也会导致过于狭隘的聚焦和过于简化的使命。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Didn't I Grow Up in the Negative World?